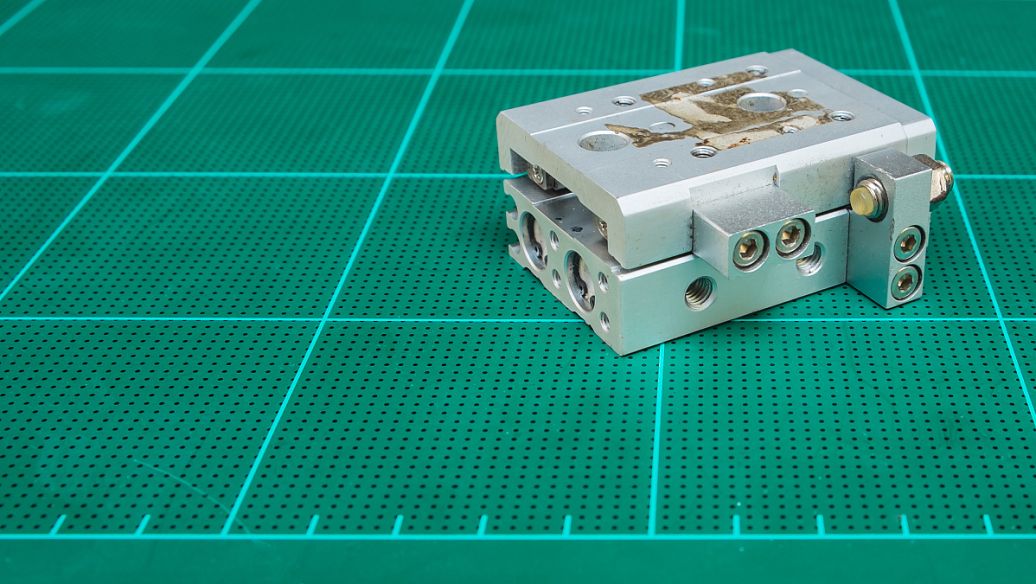狱纲吧 关注:18,447贴子:226,177
- 6回复贴,共1页
≯ L o o p≮___La Magia
BGM:天野月子-声
信じる事 なにがあっても
(相信著 不管发生什麼)
见つめる事 なにも恐れず
(凝视著 不害怕一切)
支えること どんな时でも
(支持著 不管什麼时候)
つらぬく事 なにがおこっても
(贯彻著 不管出现什麼)
狱寺隼人独自站在森林里。
夕阳已经完全落下,天际温暖的橙色回光正随着时间流逝而一点点消失不见,随之而来笼罩了一切的是死亡般静谧的夜幕。
尽管已经站了不知道多久,只穿了西服的狱寺隼人在十月微带寒意的风里仍然身姿笔挺,如果不是他的胸膛还随着呼吸有轻微的起伏,很难相信这样一动不动地站立着的真的是人而非冰冷的石雕。
“……。”
不知道又过了多久,狱寺隼人终于轻声地说了些什么。
也许是长时间的站立和寒冷的夜风让他有点僵硬,也或许是他本来就没准备让谁听到那句话吧。随着几个轻微变换的口型,那句话在出口的一瞬间就与十月的夜风一同悄然飘散了。
他抬手从衣领里拉出一条链子。吊坠是个极精致的沙漏,半个手掌大小,银色磨砂的底盘和支柱上刻着非常繁复古朴的花纹和意义不明的奇异符号。下方的玻璃球里违反常理地空无一物,上方的玻璃球里则盛满了晶莹美丽的绯红色液体。
迎着月光端详了片刻那个沙漏,狱寺隼人平静地扬起了唇角,将沙漏顶部的盘面轻轻转动了一点。
像是打开了某个开关,连接沙漏上下层的细颈被缓缓流下的第一滴液体,首次染上了绯色。
“Perdoname.(宽恕我)”
在其身影被盘旋而上的鲜红光芒完全吞噬包围而后消失不见的那一刻,低垂着视线的银发青年吐出了这样的言辞。
而空无一人的寂静森林中,聆听着那留下的最后祈求的,只有银色月光垂照中的纯黑棺柩。
什么也好,我的愿望从来只有那一个……
狱寺隼人独自在自己的卧室里醒来。
他觉得自己做了一个很长很复杂的梦,但又想不起来具体梦到了些什么,只感觉浑身上下都透着深深的疲惫。
原地呆坐了一会儿,他看了看时间,猛地窜起来换衣服洗漱,很快就把这种奇怪的疲惫感抛在了脑后。
“狱寺君今天也来得很早啊。”
泽田奈奈对在门口打转的银发少年温柔地笑起来:“纲君马上就收拾好了,要进来等他吗?”
“不麻烦了!”狱寺隼人弯腰鞠了个九十度的躬:“我在这里等十代目就可以!”
“狱寺君还是那么客气呢,”泽田奈奈笑得更加温柔了。她很喜欢这个有点笨拙又认真的孩子:“啊,准备好了吗?”
“早上好狱寺君,妈妈,我出门了——”
“纲君和狱寺君路上小心~”
狱寺隼人一般会提前五到十分钟在泽田家门口等他,两个人一起走上大概五六百米,在路口会遇到山本武(偶尔还会看到晨跑经过的了平),然后三个人一起去学校。虽然狱寺隼人对一大早就要见到山本武这件事还是颇有点不满,不过‘能和十代目一起上学’这一点足以抵消了。
今天的日程表也没有什么变化。他们互道了早安,时间还挺早,所以也不用走得太急,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慢慢往学校的方向走。是一如既往的平和日常——
“——狱寺君!”
泽田纲吉忽然出声,一把将狱寺隼人拉开。下一秒,他原来所在的位置已经被高温融化出了一个不小的坑。
“您没事吧,十代目?”
狱寺隼人转身挡在泽田纲吉身前,手上岚戒已经腾起鲜红火炎。
“我没事,但是……”
但是。
泽田纲吉皱起眉。
刚刚的一瞬间,超直感提醒了他有什么人要发动攻击。
但是奇怪的是,那攻击并不是针对他的……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
SYSTEM C·A·I的保护屏障在他们周围张开。
“敢对十代目动手的是哪个混蛋!不要藏头露尾的,自己出来!”
狱寺隼人保护性地伸开手臂,用身体遮挡着泽田纲吉,指间夹着炸弹,一边大声挑衅一边目光警惕地扫视着四周。
泽田纲吉侧耳听了片刻,扯扯狱寺隼人的衣袖。
“我想他已经走了……或者至少是暂时不会再攻击了,狱寺君。”
对自家首领的判断抱有百分之百的信任,狱寺隼人一脸不忿地收起火炎和炸药,小声嘀咕着类似于‘不知道哪个混蛋不想活了居然有胆子对十代目动手我一定会把那家伙大卸八块说起来十代目真的没有事吗我一定会好好保护十代目的谁也别想在我在的时候伤到十代目一分一毫’之类的话,继续和泽田纲吉向学校走去。
在他们背后某座楼的楼顶,有谁站直身,静静目送着两人并肩离去的背影。
孤独な心 抱えて泣いた夜も
(孤独的心 拥抱哭泣的夜)
くやしくて こらえ切つれなく 流かした泪
(后悔 按捺不住 而流下的眼泪)
请不要去。
狱寺隼人是这样说的。他这样向泽田纲吉拼命恳求——
请不要去,请千万不要去,即使能拯救家族,即使能拯救世界,无论原因为何动机为何,请不要去——
泽田纲吉只是温柔地微笑着看着他。
你知道我不能不去的,隼人。
他这样回答,琥珀色瞳子里漾着点笑意,仿佛倒映了一泓夕照。
狱寺隼人知道密鲁菲奥雷提出的会面不怀好意,泽田纲吉当然也知道。可是有什么办法呢,既然身为首领,就理当负起作为首领的责任。无论代价是什么,只要有一丝希望就不能放弃,只要有一丝希望,哪怕只有一丝希望……
我不能放弃,不能逃避。我没有这么做的资格。
无论正等待着的未来是什么,我必须要迎上前去,然后从中为家族找出唯一的一线生机……
狱寺隼人垂下视线。
他不是不知道。
只是对于他来说,最重要的终究是泽田纲吉。比起所有的一切,家人也好同伴也好,泽田纲吉一个人的意义就已经超过了余下的整个世界。与此同时,他又不可能忽视泽田纲吉的愿望。泽田纲吉有他的责任,有他的义务,有他想要做到的事情。
一直以来他所做的,是成为泽田纲吉的剑,成为他的力量,为了他的愿望而奋战。他用自己的武器,拼尽全力,将泽田纲吉护在身后。但是,当泽田纲吉的愿望与他的愿望相悖……
……我的愿望只有一个……
“请让我跟您一起去,十代目。”
他恳求,头发垂下来掩住了他一切表情,夜风一样的声音里满溢着焦虑和恳切。
“您一个人去我会担心……请至少让我陪您一起去,就算是为了您的安全也……”
泽田纲吉看起来不太情愿。
他皱起眉,像是在思考怎么拒绝对方的请求。然后对上狱寺隼人决不让步的视线,想了想,叹了口气。
“反正就算我拒绝你也不会答应的吧……算了。去收拾一下,隼人。带好东西,别的我已经安排好了。我们三个小时后出发。”
“谨遵钧命。”
他鞠了个躬,急匆匆转身出去了。
泽田纲吉在他背后苦笑着又叹了口气。他抬起手,在背后落地窗外透进来的阳光中若有所思地仔细端详掌纹,缓慢地活动着手指,一点点握紧拳又一点点松开。
他想他正站在重要的命运岔口。仅此一次,事关重大,千万人的命运正系于他一身。他已经做出了决定,最优抉择,代价最小化而利益最大化。并没有什么错误或是值得犹豫之处。但是为什么会答应隼人的这个要求,他自己似乎明白,又有些不甚清楚。
……似乎是个错误的决定。如果真的发生了什么,这个决定也许只会无意义地搭上对方的生命。没有什么利益,只有无谓的牺牲。并不是没有办法隐瞒过对方,甚至可以拒绝这个请求,狱寺隼人绝不会违逆他的意志。……那么为什么要答应……?
泽田纲吉这样想着,看着自己摊开在阳光下的手掌。皮肤白皙,手指修长,指甲被修剪得光洁完美。是一双养尊处优的手,看不出它曾经沾染过血,也看不出它握着千万人的命运。在面临无数关口的时候它都冷定平稳,握着武器或是握着笔,战胜过各种各样的敌人。然而此刻即使在温暖的阳光里它也仍然极为冰冷,指尖有不易察觉的微小颤抖。
他握紧双手,又缓缓放开,叹着气微笑着。
…………果然,作为‘泽田纲吉’的自己……仍然会感觉到恐惧。仍然会自私地希望,不需要独自一人去面对……
泽田纲吉垂下视线。他的身影在鲜烈的阳光里显得有些模糊,由于逆光而看不清表情。他的嘴唇动了动,说了句什么。
除他之外没有人听到的那句言辞,在空旷的房间之中,逐渐弥散消失……
狱寺隼人走在泽田纲吉背后。右手边,半步距离,不远不近,可以看到泽田纲吉微长的柔软棕发拂着衬衫笔挺的白色领子,轮廓线条流畅的白瓷一样的侧脸,唇角微抿,眼神放得很远,像是在想着什么,又像什么都没想。
密鲁菲奥雷的雪白大门近在咫尺。泽田纲吉停下脚步,稍稍仰起头观看门扉上装饰的精美花朵浮雕,脖颈拉成一个非常优美而脆弱的弧度。狱寺隼人一瞬间有点愣神,觉得心脏猛地一缩。他小幅度地甩甩头,似乎是要借这种动作摆脱掉大脑里的不知道什么念头,然后下意识地想走上前去替泽田纲吉拉开大门。
泽田纲吉却轻轻抬手挡下他,动作间不动声色而灵巧地反握上他的手。掌心见汗,有极细微的凉意,在他掌心不易察觉地轻轻颤抖。
他有些惊异地抬眼去看泽田纲吉,得到对方一个轻柔的微笑。那一瞬间并不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他仍然是下意识地遵循着对方眼神和肢体语言的指令,退到了他的背后。
泽田纲吉转过头去,推开了那扇门。
白兰·杰索向他们露出了满含恶意的甜美微笑。
他扣下扳机。
像连接着枪口和心脏的丝带,子弹的痕迹划破了腾起的大空火炎,近乎无声地猝然终止。鲜血的色泽突兀地划破了一片纯白的房间,在泽田纲吉的胸口如花朵盛开。
欢迎光临。
放下枪,白兰这样说着,微笑和声音都甜美得宛如蜜糖。
他身边小小的少女沉默着,面无表情地看着这一切。
失去了主人的犬会做出些什么来呢,我倒是比较好奇——
他笑着说,带着仍然面无表情的公主从容退场,留下狱寺隼人在原地,由于纷至沓来的惊恐和愤怒和绝望而濒临崩溃。
——整个世界,在眼前,在手中失去了——
绝望。
只有绝望。
被绝望席卷了。
唯一能感受到的就是绝望。
什么都做不了,什么都思考不了。
整个人完全被淹没在深沉的绝望之海中。
啊啊。这不是真的吧。不是真的吧。怎么可能呢。十代目怎么可能会死——怎么可能会死在自己的眼前呢。
……如果能够做点什么的话,如果早点意识到的话,如果阻止了十代目的话,如果自己先推开了那扇门的话,如果能够及时反应过来的话……
都是我的错。我明明能够阻止这一切的。明明能够保护十代目的。
怎么会这样……
如果能够做些什么……如果能够弥补这一切,能够拯救这一切,能够……只要能够做些什么,无论什么都可以,无论付出什么代价都可以……
十代目……
十代目…………
…………我的愿望,唯一的一个愿望……
……然后,在他的面前,出现了奇迹。
彭格列的‘时间’,玛雷的‘空间’,与阿尔柯巴雷诺的‘点’。海,贝,虹;七的三次方齐聚一堂,在那个瞬间引发的仅此一次的奇迹……
其规则有三。
其一,不得透露尚未来临之事。
其二,无法改变已经过去之事。
其三,得到什么就要付出什么。
带着泽田纲吉的遗体,他回到了彭格列。
葬礼结束之后独自在林中站到午夜时分的狱寺隼人——没有挣扎,也没有犹豫,为了唯一的那个愿望——他使用了那个奇迹。
然后,世界走上了另一条道路……吗?
(孤独的心 拥抱哭泣的夜)
くやしくて こらえ切つれなく 流かした泪
(后悔 按捺不住 而流下的眼泪)
请不要去。
狱寺隼人是这样说的。他这样向泽田纲吉拼命恳求——
请不要去,请千万不要去,即使能拯救家族,即使能拯救世界,无论原因为何动机为何,请不要去——
泽田纲吉只是温柔地微笑着看着他。
你知道我不能不去的,隼人。
他这样回答,琥珀色瞳子里漾着点笑意,仿佛倒映了一泓夕照。
狱寺隼人知道密鲁菲奥雷提出的会面不怀好意,泽田纲吉当然也知道。可是有什么办法呢,既然身为首领,就理当负起作为首领的责任。无论代价是什么,只要有一丝希望就不能放弃,只要有一丝希望,哪怕只有一丝希望……
我不能放弃,不能逃避。我没有这么做的资格。
无论正等待着的未来是什么,我必须要迎上前去,然后从中为家族找出唯一的一线生机……
狱寺隼人垂下视线。
他不是不知道。
只是对于他来说,最重要的终究是泽田纲吉。比起所有的一切,家人也好同伴也好,泽田纲吉一个人的意义就已经超过了余下的整个世界。与此同时,他又不可能忽视泽田纲吉的愿望。泽田纲吉有他的责任,有他的义务,有他想要做到的事情。
一直以来他所做的,是成为泽田纲吉的剑,成为他的力量,为了他的愿望而奋战。他用自己的武器,拼尽全力,将泽田纲吉护在身后。但是,当泽田纲吉的愿望与他的愿望相悖……
……我的愿望只有一个……
“请让我跟您一起去,十代目。”
他恳求,头发垂下来掩住了他一切表情,夜风一样的声音里满溢着焦虑和恳切。
“您一个人去我会担心……请至少让我陪您一起去,就算是为了您的安全也……”
泽田纲吉看起来不太情愿。
他皱起眉,像是在思考怎么拒绝对方的请求。然后对上狱寺隼人决不让步的视线,想了想,叹了口气。
“反正就算我拒绝你也不会答应的吧……算了。去收拾一下,隼人。带好东西,别的我已经安排好了。我们三个小时后出发。”
“谨遵钧命。”
他鞠了个躬,急匆匆转身出去了。
泽田纲吉在他背后苦笑着又叹了口气。他抬起手,在背后落地窗外透进来的阳光中若有所思地仔细端详掌纹,缓慢地活动着手指,一点点握紧拳又一点点松开。
他想他正站在重要的命运岔口。仅此一次,事关重大,千万人的命运正系于他一身。他已经做出了决定,最优抉择,代价最小化而利益最大化。并没有什么错误或是值得犹豫之处。但是为什么会答应隼人的这个要求,他自己似乎明白,又有些不甚清楚。
……似乎是个错误的决定。如果真的发生了什么,这个决定也许只会无意义地搭上对方的生命。没有什么利益,只有无谓的牺牲。并不是没有办法隐瞒过对方,甚至可以拒绝这个请求,狱寺隼人绝不会违逆他的意志。……那么为什么要答应……?
泽田纲吉这样想着,看着自己摊开在阳光下的手掌。皮肤白皙,手指修长,指甲被修剪得光洁完美。是一双养尊处优的手,看不出它曾经沾染过血,也看不出它握着千万人的命运。在面临无数关口的时候它都冷定平稳,握着武器或是握着笔,战胜过各种各样的敌人。然而此刻即使在温暖的阳光里它也仍然极为冰冷,指尖有不易察觉的微小颤抖。
他握紧双手,又缓缓放开,叹着气微笑着。
…………果然,作为‘泽田纲吉’的自己……仍然会感觉到恐惧。仍然会自私地希望,不需要独自一人去面对……
泽田纲吉垂下视线。他的身影在鲜烈的阳光里显得有些模糊,由于逆光而看不清表情。他的嘴唇动了动,说了句什么。
除他之外没有人听到的那句言辞,在空旷的房间之中,逐渐弥散消失……
狱寺隼人走在泽田纲吉背后。右手边,半步距离,不远不近,可以看到泽田纲吉微长的柔软棕发拂着衬衫笔挺的白色领子,轮廓线条流畅的白瓷一样的侧脸,唇角微抿,眼神放得很远,像是在想着什么,又像什么都没想。
密鲁菲奥雷的雪白大门近在咫尺。泽田纲吉停下脚步,稍稍仰起头观看门扉上装饰的精美花朵浮雕,脖颈拉成一个非常优美而脆弱的弧度。狱寺隼人一瞬间有点愣神,觉得心脏猛地一缩。他小幅度地甩甩头,似乎是要借这种动作摆脱掉大脑里的不知道什么念头,然后下意识地想走上前去替泽田纲吉拉开大门。
泽田纲吉却轻轻抬手挡下他,动作间不动声色而灵巧地反握上他的手。掌心见汗,有极细微的凉意,在他掌心不易察觉地轻轻颤抖。
他有些惊异地抬眼去看泽田纲吉,得到对方一个轻柔的微笑。那一瞬间并不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他仍然是下意识地遵循着对方眼神和肢体语言的指令,退到了他的背后。
泽田纲吉转过头去,推开了那扇门。
白兰·杰索向他们露出了满含恶意的甜美微笑。
他扣下扳机。
像连接着枪口和心脏的丝带,子弹的痕迹划破了腾起的大空火炎,近乎无声地猝然终止。鲜血的色泽突兀地划破了一片纯白的房间,在泽田纲吉的胸口如花朵盛开。
欢迎光临。
放下枪,白兰这样说着,微笑和声音都甜美得宛如蜜糖。
他身边小小的少女沉默着,面无表情地看着这一切。
失去了主人的犬会做出些什么来呢,我倒是比较好奇——
他笑着说,带着仍然面无表情的公主从容退场,留下狱寺隼人在原地,由于纷至沓来的惊恐和愤怒和绝望而濒临崩溃。
——整个世界,在眼前,在手中失去了——
绝望。
只有绝望。
被绝望席卷了。
唯一能感受到的就是绝望。
什么都做不了,什么都思考不了。
整个人完全被淹没在深沉的绝望之海中。
啊啊。这不是真的吧。不是真的吧。怎么可能呢。十代目怎么可能会死——怎么可能会死在自己的眼前呢。
……如果能够做点什么的话,如果早点意识到的话,如果阻止了十代目的话,如果自己先推开了那扇门的话,如果能够及时反应过来的话……
都是我的错。我明明能够阻止这一切的。明明能够保护十代目的。
怎么会这样……
如果能够做些什么……如果能够弥补这一切,能够拯救这一切,能够……只要能够做些什么,无论什么都可以,无论付出什么代价都可以……
十代目……
十代目…………
…………我的愿望,唯一的一个愿望……
……然后,在他的面前,出现了奇迹。
彭格列的‘时间’,玛雷的‘空间’,与阿尔柯巴雷诺的‘点’。海,贝,虹;七的三次方齐聚一堂,在那个瞬间引发的仅此一次的奇迹……
其规则有三。
其一,不得透露尚未来临之事。
其二,无法改变已经过去之事。
其三,得到什么就要付出什么。
带着泽田纲吉的遗体,他回到了彭格列。
葬礼结束之后独自在林中站到午夜时分的狱寺隼人——没有挣扎,也没有犹豫,为了唯一的那个愿望——他使用了那个奇迹。
然后,世界走上了另一条道路……吗?
10代目がもしも 不安で负けそうならば
(假如10代目 因不安而快挫败的话)
その暗をすべて オレが爆破する
(那些黑暗 我会全部破坏掉)
狱寺隼人睁开眼睛。
映入眼帘的是他在彭格列总部的房间。还是老样子,地板上乱七八糟散着几件没功夫扔到待收的洗衣篮里的脏衣服,咖啡杯和糖包,书和文件和电脑一起摞在窗台上或者桌面上,窗帘拉着,整个房间昏暗一片,看起来总之就是二十来岁单身男性上班族惯有的那么个样子,压根儿没有丝毫高级黑手党干部的风范。
不过他现在并没有精力关心那个,几乎是在确认了自己所在地点的一瞬间就一把抄起了手机,看到显示的日期——2015年10月16日——之后才带着稍微安心的表情长长吐了口气。
……回来了。虽然只是提前了两天,但是回来了……能赶得上。
还来得及。
简单洗漱了一下,把自己的外表打理到可以见人的最低限度,狱寺隼人大步离开了房间,飞快走向首领办公室。
“隼人?”
泽田纲吉有些意外地抬起头看他:“正好你来了。我准备去和白兰·杰索谈判,家族的内务暂时就……”
“不行!”
首次用这样激烈的语气反对,狱寺隼人焦虑地摇摇头:“……和密鲁菲奥雷的首领谈判?您亲自去?——这不行,十代目!”
泽田纲吉眨眨眼。他想到过狱寺隼人会反对,但是没想过他的态度会如此激烈且坚决。
“白兰也是首领,隼人,而且实话说,现在是他们占上风。如果我不亲自去,密鲁菲奥雷就可以说我们有失诚意,把战争的责任全都归咎于我们。那样会更麻烦。”
的确。那样会使原本就已经岌岌可危的彭格列再失去不少同盟家族的支援,只会更进一步地踏入绝境。
……但是他不能给白兰那个机会。只有那个绝对不行。
“……那么,至少换个地方,十代目。”他坚决地摇摇头:“至少您绝对不能去密鲁菲奥雷的总部——那太危险了,绝对不行——而且我要陪您一起去,带上您的直属卫队。”
“……”
“请您注意自身的安全……对我来说,您的安全是最重要的事啊,十代目。”
狱寺隼人如此说。
对我来说,您才是最重要的事啊。
也许是被他声音里不知来源的深切沉痛惊到,泽田纲吉低头想了想,叹了口气。
“好吧。我会和白兰交涉的。不用担心,隼人。”
他的微笑非常柔和,语调也是,带着淡淡的叹息意味。
“我会尽力好好活下去的。安心,我也不想英年早逝啊,不要这样看我。”笑着摆摆手,泽田纲吉重又低下头去:“现在就加紧把事情做完吧?”
踏出首领办公室的一刻,狱寺隼人的表情就沉重了下来。
重来一次,他才看清了泽田纲吉的眼神。那眼神很熟悉,因为不久前他才在自己的眼里见到过。
仿佛夕照一样盈盈地漾着光的,那并不是他通常所见的温柔笑意。其中蕴含的是死的觉悟——已经知道很可能会死。然而仍要义无反顾地独身前往,踏上这条有去无回的单行道——
泽田纲吉的愿望是守护所有人。为了这个愿望,牺牲他自己也没关系……是这样的吧。
“可是我的世界没有那么大啊,十代目。”
他仰起头长长吐了口气,露出个苦笑。
不能违背首领的命令,他能做的只有全力加强防卫。千挑万选的首领卫队,对会面地点的反复调查,设想可能的进攻策略和防备方式……压在他心上的不仅仅是可能来临的危险,铭刻在心的回忆无时无刻不紧紧缠绕着他,压力太大,仅仅是连轴转了一晚他就已经开始头晕胃疼,只好将不太重要的活交给副手,自己去给泽田纲吉帮忙。晚上躺在床上睡不着,内心的焦虑情绪高涨,却逼着自己合上眼好好休息一晚,养足精神预防第二天的突发情况。
“请您务必答应我,”10月18日,他和泽田纲吉坐在车上的时候,他这样说:“如果发生了什么……不管发生了什么,请您务必,保住自己的生命。”
“我求您——只是以狱寺隼人的身份,十代目,求您一定要回来。”
和上一次不同,这次的谈判设在中立地带。双方都把武装部队留在了场外,不带武器,孤身进入谈判场。
白兰答应得太过爽快,反而让狱寺隼人感到了隐隐的不安。他在门口焦虑地来回踱步,试图压制住内心翻涌的情绪而不得,反而使得部下们也被感染得焦躁不安。他想要控制,却有心无力。
说到底,泽田纲吉的死亡……即使是想象都会让他失去所有的冷静,何况曾亲眼目睹。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没有任何事情发生,部下们逐渐安下心来,狱寺隼人反而觉得愈发不安。他不相信白兰会真的不做一点小动作,却不知道对方究竟会在哪里动手脚。
今天一定会出事,一定会出事。泽田纲吉一定会有生命危险。
他知道。他确信。
但是那是‘不能说出口’的,是‘尚未发生’的。
是他必须独立承担的记忆。
在所有人都几乎放下心觉得一切平安的这个时候,他则感到了暗处正虎视眈眈的危机。
他的电话突然响了起来。他接起来,对面是绵软甜美的糖果一样的让他刻骨铭心的声音——
“喂喂,是狱寺隼人君~吗~?♪”
“一道选择题~彭格列基地附近埋了炸药,但是纲吉君现在在我这里哦~?”
“给本部打电话,或者是现在进入会场,请选一个吧~”
“你有一分钟的考虑时间哦♪”
“……”
他短暂地犹豫了几秒。
现在冲进会场,谈判失败的结果白兰完全可以归结到他们身上。
背后是,家族本部的基地。只要打电话回去,还来得及转移人员……
那是彭格列,那里有他的同伴,朋友和家人,那里是……那里是泽田纲吉拼命想要保护的地方……
但是……
他下死命握住手机,停顿片刻,转身。
我的愿望只有那一个……
鲜红的岚之火焰燃烧起来,System C·A·I随时可以发动,猫形的瓜轻巧无声地落在他脚边。
没有人,没有人,没有人,没有人,整个谈判会场空无一人,死寂宛如坟墓。
他推开雪白的大门。
白兰·杰索向他露出了满含恶意的甜美微笑。
“猜错了啊,狱寺君。”
他轻声说。
狱寺隼人听到身后传来奔跑的脚步声。
白兰抬起枪口。
有人从背后跑过来——推开他——
燃起的火焰被子弹划开——
泽田纲吉转过头冲他勉力微笑了一下。然后那双琥珀色的眼睛慢慢闭上了,他胸口有花逐渐开出来,鲜血的红色,在一片纯白的房间里简直刺人眼目。
“Lo siento(我很遗憾)”
白兰笑着冲他耸耸肩,转身消失在了毫无杂质的雪白之中。
……十代目。没关系的,十代目。
我还有机会。还有办法……还有时间。
约好了,一定能够拯救您……
无论多少次也……
他拉出那个沙漏,再次转动了底盘。
银发的身影消失在绯红光芒中时,第一滴鲜红的液体坠落进了下层沙漏之中。
(假如10代目 因不安而快挫败的话)
その暗をすべて オレが爆破する
(那些黑暗 我会全部破坏掉)
狱寺隼人睁开眼睛。
映入眼帘的是他在彭格列总部的房间。还是老样子,地板上乱七八糟散着几件没功夫扔到待收的洗衣篮里的脏衣服,咖啡杯和糖包,书和文件和电脑一起摞在窗台上或者桌面上,窗帘拉着,整个房间昏暗一片,看起来总之就是二十来岁单身男性上班族惯有的那么个样子,压根儿没有丝毫高级黑手党干部的风范。
不过他现在并没有精力关心那个,几乎是在确认了自己所在地点的一瞬间就一把抄起了手机,看到显示的日期——2015年10月16日——之后才带着稍微安心的表情长长吐了口气。
……回来了。虽然只是提前了两天,但是回来了……能赶得上。
还来得及。
简单洗漱了一下,把自己的外表打理到可以见人的最低限度,狱寺隼人大步离开了房间,飞快走向首领办公室。
“隼人?”
泽田纲吉有些意外地抬起头看他:“正好你来了。我准备去和白兰·杰索谈判,家族的内务暂时就……”
“不行!”
首次用这样激烈的语气反对,狱寺隼人焦虑地摇摇头:“……和密鲁菲奥雷的首领谈判?您亲自去?——这不行,十代目!”
泽田纲吉眨眨眼。他想到过狱寺隼人会反对,但是没想过他的态度会如此激烈且坚决。
“白兰也是首领,隼人,而且实话说,现在是他们占上风。如果我不亲自去,密鲁菲奥雷就可以说我们有失诚意,把战争的责任全都归咎于我们。那样会更麻烦。”
的确。那样会使原本就已经岌岌可危的彭格列再失去不少同盟家族的支援,只会更进一步地踏入绝境。
……但是他不能给白兰那个机会。只有那个绝对不行。
“……那么,至少换个地方,十代目。”他坚决地摇摇头:“至少您绝对不能去密鲁菲奥雷的总部——那太危险了,绝对不行——而且我要陪您一起去,带上您的直属卫队。”
“……”
“请您注意自身的安全……对我来说,您的安全是最重要的事啊,十代目。”
狱寺隼人如此说。
对我来说,您才是最重要的事啊。
也许是被他声音里不知来源的深切沉痛惊到,泽田纲吉低头想了想,叹了口气。
“好吧。我会和白兰交涉的。不用担心,隼人。”
他的微笑非常柔和,语调也是,带着淡淡的叹息意味。
“我会尽力好好活下去的。安心,我也不想英年早逝啊,不要这样看我。”笑着摆摆手,泽田纲吉重又低下头去:“现在就加紧把事情做完吧?”
踏出首领办公室的一刻,狱寺隼人的表情就沉重了下来。
重来一次,他才看清了泽田纲吉的眼神。那眼神很熟悉,因为不久前他才在自己的眼里见到过。
仿佛夕照一样盈盈地漾着光的,那并不是他通常所见的温柔笑意。其中蕴含的是死的觉悟——已经知道很可能会死。然而仍要义无反顾地独身前往,踏上这条有去无回的单行道——
泽田纲吉的愿望是守护所有人。为了这个愿望,牺牲他自己也没关系……是这样的吧。
“可是我的世界没有那么大啊,十代目。”
他仰起头长长吐了口气,露出个苦笑。
不能违背首领的命令,他能做的只有全力加强防卫。千挑万选的首领卫队,对会面地点的反复调查,设想可能的进攻策略和防备方式……压在他心上的不仅仅是可能来临的危险,铭刻在心的回忆无时无刻不紧紧缠绕着他,压力太大,仅仅是连轴转了一晚他就已经开始头晕胃疼,只好将不太重要的活交给副手,自己去给泽田纲吉帮忙。晚上躺在床上睡不着,内心的焦虑情绪高涨,却逼着自己合上眼好好休息一晚,养足精神预防第二天的突发情况。
“请您务必答应我,”10月18日,他和泽田纲吉坐在车上的时候,他这样说:“如果发生了什么……不管发生了什么,请您务必,保住自己的生命。”
“我求您——只是以狱寺隼人的身份,十代目,求您一定要回来。”
和上一次不同,这次的谈判设在中立地带。双方都把武装部队留在了场外,不带武器,孤身进入谈判场。
白兰答应得太过爽快,反而让狱寺隼人感到了隐隐的不安。他在门口焦虑地来回踱步,试图压制住内心翻涌的情绪而不得,反而使得部下们也被感染得焦躁不安。他想要控制,却有心无力。
说到底,泽田纲吉的死亡……即使是想象都会让他失去所有的冷静,何况曾亲眼目睹。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没有任何事情发生,部下们逐渐安下心来,狱寺隼人反而觉得愈发不安。他不相信白兰会真的不做一点小动作,却不知道对方究竟会在哪里动手脚。
今天一定会出事,一定会出事。泽田纲吉一定会有生命危险。
他知道。他确信。
但是那是‘不能说出口’的,是‘尚未发生’的。
是他必须独立承担的记忆。
在所有人都几乎放下心觉得一切平安的这个时候,他则感到了暗处正虎视眈眈的危机。
他的电话突然响了起来。他接起来,对面是绵软甜美的糖果一样的让他刻骨铭心的声音——
“喂喂,是狱寺隼人君~吗~?♪”
“一道选择题~彭格列基地附近埋了炸药,但是纲吉君现在在我这里哦~?”
“给本部打电话,或者是现在进入会场,请选一个吧~”
“你有一分钟的考虑时间哦♪”
“……”
他短暂地犹豫了几秒。
现在冲进会场,谈判失败的结果白兰完全可以归结到他们身上。
背后是,家族本部的基地。只要打电话回去,还来得及转移人员……
那是彭格列,那里有他的同伴,朋友和家人,那里是……那里是泽田纲吉拼命想要保护的地方……
但是……
他下死命握住手机,停顿片刻,转身。
我的愿望只有那一个……
鲜红的岚之火焰燃烧起来,System C·A·I随时可以发动,猫形的瓜轻巧无声地落在他脚边。
没有人,没有人,没有人,没有人,整个谈判会场空无一人,死寂宛如坟墓。
他推开雪白的大门。
白兰·杰索向他露出了满含恶意的甜美微笑。
“猜错了啊,狱寺君。”
他轻声说。
狱寺隼人听到身后传来奔跑的脚步声。
白兰抬起枪口。
有人从背后跑过来——推开他——
燃起的火焰被子弹划开——
泽田纲吉转过头冲他勉力微笑了一下。然后那双琥珀色的眼睛慢慢闭上了,他胸口有花逐渐开出来,鲜血的红色,在一片纯白的房间里简直刺人眼目。
“Lo siento(我很遗憾)”
白兰笑着冲他耸耸肩,转身消失在了毫无杂质的雪白之中。
……十代目。没关系的,十代目。
我还有机会。还有办法……还有时间。
约好了,一定能够拯救您……
无论多少次也……
他拉出那个沙漏,再次转动了底盘。
银发的身影消失在绯红光芒中时,第一滴鲜红的液体坠落进了下层沙漏之中。
“隼人。”
时间是2024年的五月深春,泽田纲吉背对着京都的花雨,在钟声里喊他。
“我需要你解释一下。”
他皱着眉,十指交叉放在身前,琥珀色眼睛里浮动着一点疑惑不解的光。
“你是觉得密鲁菲奥雷会产生威胁吗?如果你坚持这样认为,即使不理解,我可能也会采纳你的意见。”
“但是,没有得到我的同意,调用家族力量针对对方。你知道这可能会带来多大麻烦……”
“这不是正式会议。我希望你解释一下,隼人,为什么这么做?”
狱寺隼人的手微微颤抖起来。
他沉默着,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我必须要这样做。我不敢冒险让他发展起来,我不知道他知道多少。我必须要这样做,就算我知道这样做绝对不可饶恕,但是我必须……
我必须……
我必须这么做……
我…………
房间里弥漫着长久的,冰冷的沉默。
在这样的沉默里,那双漂亮的琥珀色眼睛终于一点点暗了下去。
“我相信你。”他说。
狱寺隼人不可置信地抬头看他,而泽田纲吉报以一个忧伤的微笑。
“但是你知道,隼人,我也有不能做的事情……”
事情就像是没有发生过一样,这么结束了。但狱寺隼人知道这更糟糕。
泽田纲吉大概也难以决定要如何处理他,毕竟这并不是公开了的,必须由首领表态的事情。但毫无疑问,这种先例决不能开。在两种可能的选择间举棋不定的结果就是他被不动声色地冷落了,泽田纲吉有意无意地回避着他,甚至相处一天都不会有几次眼神交汇。
然而,对现在的狱寺隼人而言,比起愧疚和痛苦,他更多地感到极度焦急。
被排除出核心决策圈,他不再能及时准确地得到密鲁菲奥雷和白兰的动向消息。泽田纲吉离开本部办公的时候不再要求他陪同。资讯不畅,又不能直接陪同,只要想象可能产生的危险,哪怕只是想象一下……
真的不能再失去了。
他紧紧握住那个沙漏吊坠。鲜红的液体已经在下层积蓄了大半,而涓涓细流仍然在毫不停歇地滴落下来。
越来越快了。
能付出的代价已经不多。
没有太多机会了……
我想要保护您啊。
唯一的愿望。
无论付出什么。
我唯一的愿望,十代目,我想要保护您啊……!
他知道的时候,事情已经发生了。
“十代目去了西西里?”
狱寺隼人平静地这么问。
得到了肯定答复的那一刻,他甚至平静地点了点头,随后一言不发地转身离开。
不再贴身协助泽田纲吉,离开核心决策圈,他错过了太多的动向资讯,但能够得到的资讯已经足以判断——没有别的可能。这种时候需要泽田纲吉回去西西里,只会是因为白兰。
尽管离他记忆中的那个日子还早,他仍然感到了一阵寒意,在京都的夏日里从他的心底幽幽地漫上来。
调用了彭格列的专机赶回西西里,时差都没有倒就立刻上车前往会议地点。什么都来不及想,什么都没办法做,只能向不知道是否存在的神明拼命祈祷,请不要,请千万不要,最糟糕的,反复一遍一遍目睹过的那个未来,请千万不要再走到那里去。
无论要付出什么代价都可以,什么都可以,已经付出了这么多,这么多了呀,难道还不足够吗。如果必须要等价交换,就拿走我的生命也可以,既然是已经准备好了放上交易天平的东西,提前拿走也可以,只要能实现那个愿望,唯一的一个——
然而若是有神明,他的呼唤也并没有,传达到神明的耳中——
迎接千里迢迢赶来的这群精英们的,是战火和烽烟,枪弹和火焰,同僚们的鲜血和惨叫。
“我建议过你好好考虑的,十代岚守君♪”
白兰的声音在他耳边里挥之不去。
“纲吉君当然相信你呀~可是作为教父,他总有教父要做的事情,不是吗~♪”
“从你决定违背他的意愿开始,这一天就已经注定要来了~♪”
不想听到。
但是又清楚地意识到,并没有错。
的确是由于自己的原因,才导致这样的结果。
从一开始就是这样。
如果自己能做得更好一点,如果能做得更好一点,哪怕是不要犯错……
很多事情就能够避免了吧。
很多事情就能够做到了吧。
那个愿望,唯一的愿望……
是自己的原因。
是因为自己。
口口声声说着想要守护,想要拯救,无论如何,无论如何……却因为自己的无能,导致一次一次,越来越悲惨的未来……
“隼人。”
时间是2024年的十一月。西西里温暖的阳光被阻隔在洁白的建筑物外,泽田纲吉微微合着眼睛,在他的怀里,用温和而疲惫的声音喊他。
“真抱歉……我该更相信你一点的。”
“虽然不知道为什么,你应该也是有自己的理由的吧。”
剧痛和失血让他几乎没有力气再说下去了。那双美丽的琥珀色眼睛,漾着夕照一样盈盈的光,正一点点逐渐黯淡。
“还有……一件事……一定要拜托你。”
“活下去啊,隼人。就当是替我……你要活下去,隼人。”
不是没看到那个枪伤。和之前的每一次都不同,那不是普通的子弹造成的伤口。
穿透腹部的贯通伤,原本用晴之火焰暂时促进伤口愈合止血,尽快送回措施完备的地方进行治疗,存活几率仍然很高。但是这是……达姆弹的创口啊……!子弹进入人体后爆炸,产生十几倍甚至几十倍的喇叭状空腔,血液迅速流失,空气涌入体内,大量弹片留在体内造成铅中毒甚至水银中毒;比内脏出血都要可怕得多,可怕得多……!即使是六道骸或者库洛姆在这里,对这样的伤势也根本无能为力……一般情况下,没办法及时治疗,对这样的伤者给他们一个痛快都好过继续让他们忍受这种痛苦的死亡……
但是我怎么能……狱寺隼人怎么能……
拥抱着的人在颤抖,在一点点冰凉下去。满地都是血,人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多血呢,比火焰还要纯正的绯红,简直红得有些刺眼了。眉头紧皱着,美丽的琥珀色眼睛已经闭上了,手指还扶着他的手臂,但是已经再没有力气收紧它们来分担痛楚。喉咙深处传出低低的,强自压抑着的极痛苦的声音……
他不敢动。哪怕只是稍微移动一点点,都可能会牵扯到泽田纲吉的伤处。他想要为泽田纲吉分担痛苦,或者做些什么,来让他感觉好一点,但是他做不到。明明近在咫尺却不能触碰,他什么也做不了,什么也做不到,只能徒劳地看着泽田纲吉的生命从他的双手中流逝而去。
非常疼吧,十代目,非常疼吗……一定是非常疼,非常疼,这样的伤一定非常疼吧……
狱寺隼人抬起手,非常非常小心地,像是要抚摸什么一触即碎的珍宝一样,轻轻抚上了泽田纲吉的额头。而后掠过眉眼,鼻梁,脸颊,唇瓣,珍重热烈,又那样轻柔地抚摸过他面容的每一寸细节。
“……十代目。”
他轻声道,而后嘴唇动了动,不知道说了些什么。
雪亮的阳光从窗外落进来。大片鲜红的血泊和室内纯白的装饰中间,狱寺隼人的银发泛出一圈鲜烈的光泽。他的面庞上像是有水光一闪,旋即也消失不见了。
泽田纲吉枕着他的膝盖,在雪一样明亮耀眼的阳光里静静合着眼睛。然后他俯下身亲吻了对方的额头,手腕稳如磐石,将枪口对准了泽田纲吉的心脏。
狱寺隼人扣下扳机。
枪声响起。
他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对世界的感知似乎都消泯在了那一声枪响里。也许是过了一会,也许是过了很长时间,一片空白的世界才慢慢地,一点点地,回到他的意识里来。
但是那些都不重要,已经都不重要了。
“Perdoname.(宽恕我)”
狱寺隼人轻声说。
他拉出那个沙漏,丝毫不在意上半部分的红色液体所剩已经不多,又一次转动了底盘,身影随之消失在鲜红的光芒里。
作者已经死于这篇文。
重复一遍。
作者和她的智商都已经死于这篇文。
如果有任何BUG/哪里不对/OOC/情节硬伤/人物跑错片场/逻辑没上线等问题,一定是因为作者脑子有病/智商掉线/智商全面掉线/是个神经病/脑细胞全部死亡/已经死了。
谢谢大家。
重复一遍。
作者和她的智商都已经死于这篇文。
如果有任何BUG/哪里不对/OOC/情节硬伤/人物跑错片场/逻辑没上线等问题,一定是因为作者脑子有病/智商掉线/智商全面掉线/是个神经病/脑细胞全部死亡/已经死了。
谢谢大家。
扫二维码下载贴吧客户端
下载贴吧APP
看高清直播、视频!
看高清直播、视频!
贴吧热议榜
- 1老外学中文不看弱智吧等于白学2328660
- 2黑神话惊喜贺岁片隐藏彩蛋2244658
- 3如何评价OW2这波回归补偿?1615852
- 4来了中文软件就给我说中文1428624
- 5中美网友对账发现对不上1031030
- 6海贼王1136话情报露出1003150
- 7一月新番点评871032
- 8断电断网能否解决缅北电诈828437
- 9有没有发现空耳文化逐渐衰退了664268
- 10女版donk横空出世625002